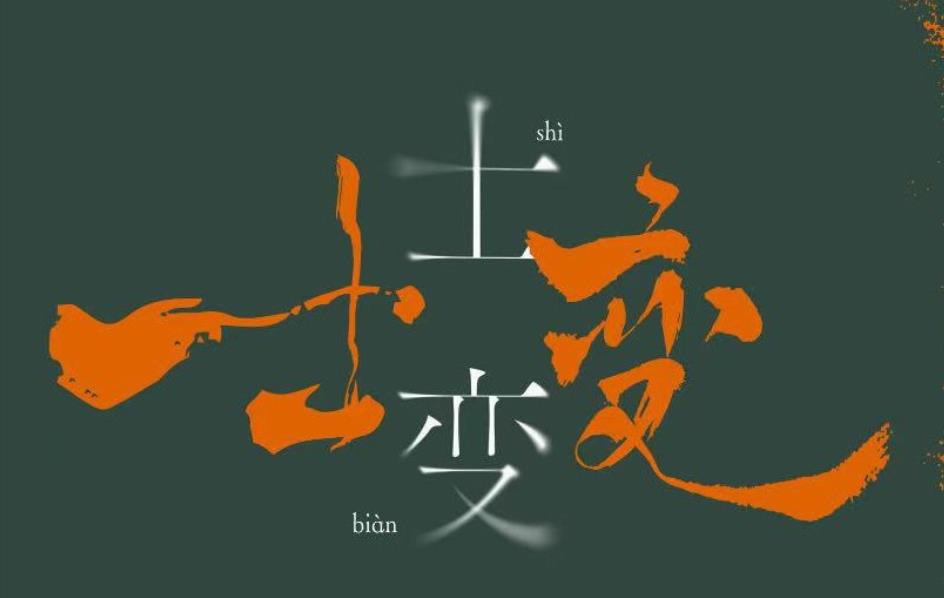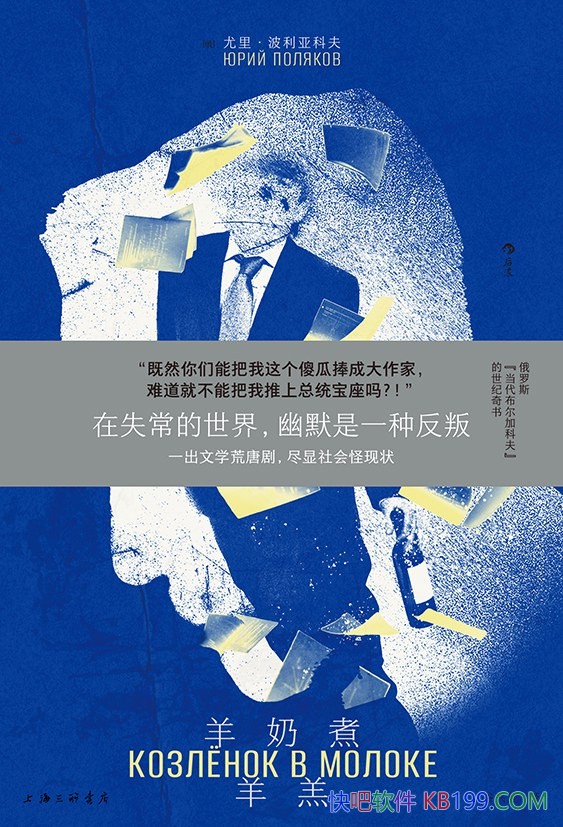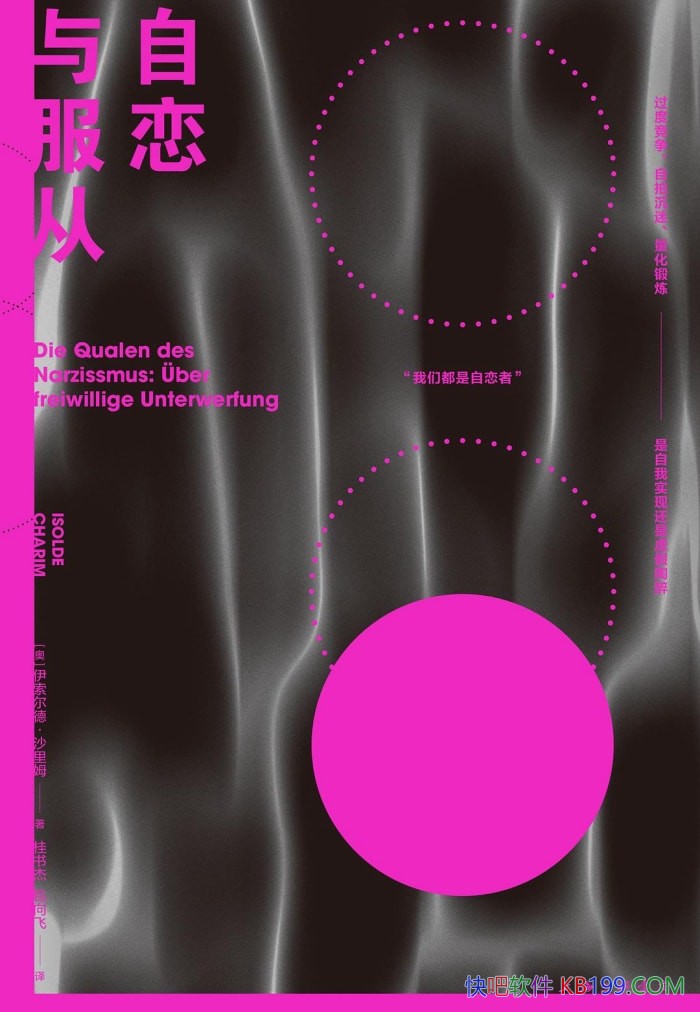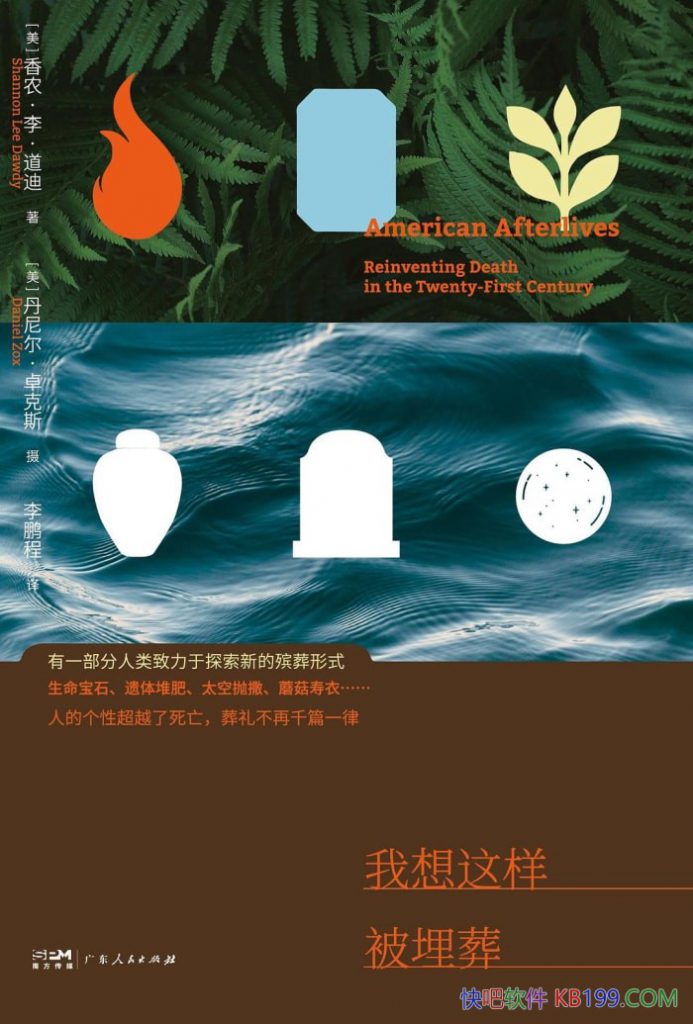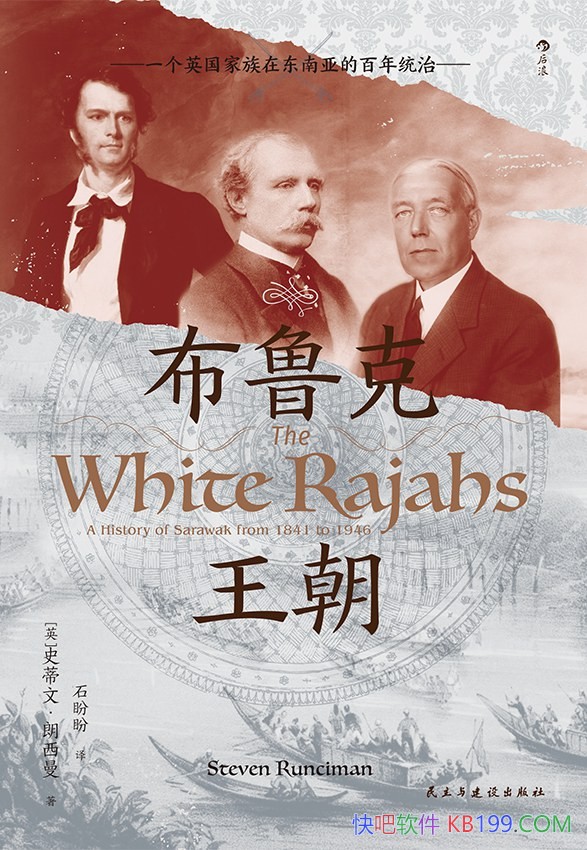《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一辈子献给了新疆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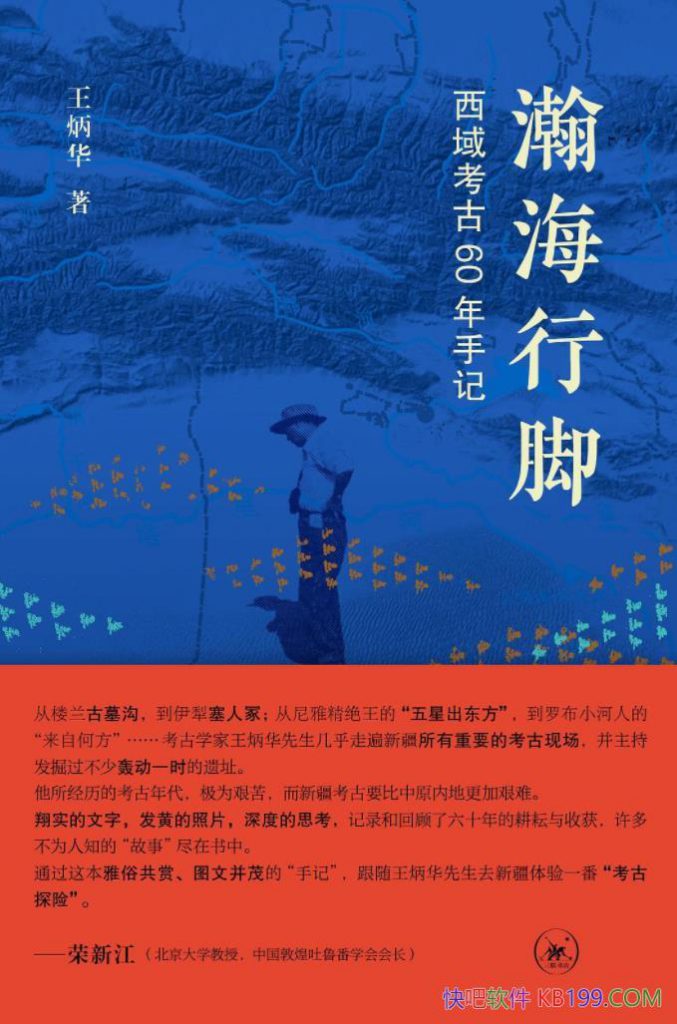
从楼兰古墓沟,到伊犁塞人冢;从尼雅精绝王的“五星出东方”,到罗布小河的“来自何方”……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几乎走遍新疆所有重要的考古现场,主持发掘过不少轰动一时的遗址。他所经历的考古年代,极为艰苦,而新疆考古要比中原内地更加艰难。在新疆考古的学术史上,王炳华先生是占有篇幅最多的几位先驱之一。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王炳华先生西域考古60年手记——《瀚海行脚》,读者有机会通过阅读翔实的文字和发黄的照片,跟随他去新疆体验一番“考古探险”。
1960年,也有一位来自江苏南通的青年,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一批考古专业的毕业生,踏上了奔赴新疆的路途,从此与那里结缘60载——40年田野考古加上20年研究教学,一辈子献给了新疆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疆考古所前所长、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把自己这60年的新疆考古生涯称为“瀚海行脚”,同名图书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是为“西域考古60年手记”。
15篇考古手记,26万余字,150多张插图照片,王炳华说,《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以下简称《瀚海行脚》)是一本“主要得之于个人体验、工作,植根在新疆广阔考古舞台上的小书”。细读其内容才发现,这本书的时间跨度覆盖了从1960年发掘阿斯塔那晋-唐古墓,一直到近些年的书写与思考,不仅记录和叙述了他从开创伊犁河流域考古开始,到发现孔雀河青铜时代墓葬、主持并参与楼兰、尼雅、克里雅、丹丹乌里克、小河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过程中的所见、所思与所感,而且呈现了他一生投身考古事业不断求索的时间脉络。
1958年,国家在新疆成立了8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其中之一就是考古研究所。当时仅有几位博物馆筹备组人员作为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王炳华正是了解到考古所紧急请求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学生后,主动申请从事这一工作。1960年夏他来到乌鲁木齐,当时“新疆考古研究所”既无办公室,也无实际在职人员。作为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立即带领各县调来的学员进入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进行考古实习,结束后又马上单枪匹马地开始了对交河故城的调查。条件艰苦、设备有限,王炳华不仅学会并习惯了骑马跋涉在地广人稀、沙漠戈壁纵横的野外,也在与居民的沟通交流中学习了当地语言,接触和了解了许多民风民俗。王炳华对新疆大地厚积的考古沃土充满了感激,他说,这里干燥的环境利于古代文物的保护与留存,他所踏入的时代也为新中国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崭新舞台,更不用说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都是让他有幸“走”到诸多重要遗存面前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尤其是,1979年王炳华率队找到了楼兰古城,2000年退休前发现了神秘的小河墓地……每每回忆起这些艰苦但又辉煌的时刻,王炳华都有说不完的感慨。
通过阅读《瀚海行脚》一书的目录,我们便可一窥王炳华在新疆“行脚”数十载的考古经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王炳华等人即对伊犁河流域进行发掘,他提出了乌孙考古文化的概念。70年代末,他主持发掘了阿拉沟的多处墓葬,并撰文详述了其为塞人考古文化的观点,极大促进了对新疆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存的讨论。1987年,王炳华在呼图壁县发现康家石门子岩画。岩画揭示的古人生殖崇拜思想,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对新疆地区生殖崇拜和古人精神世界的研究也成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后来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哈密五堡古尸、楼兰古墓沟出土的“楼兰美女”及“太阳墓”墓葬遗存所呈现出的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经由王炳华的分析论述,让异质文明碰撞后产生的混融与合一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与总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炳华还曾组织带领中日、中法联合考古队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尼雅遗址和克里雅河流域进行了发掘与考察。精绝王陵的发掘被评为当年(1995)考古十大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宝。2000年,王炳华与考古队在骑骆驼深入沙漠的第五天,成功发现了小河墓地,再一次将沉睡的丝绸之路古代遗存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同一年,王炳华从田野考古一线退休,但仍继续对西域文史领域的思考,追索新疆作为欧亚大陆古代东西方文化桥梁的非凡意义。他关注古代文明遗存透露出的环境变迁与绿洲农业发展历程,撰写了一系列考察自然环境改变与农耕水利相关的论文,还结合传世史籍记载对墓葬文物进行分析,进一步阐释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与发展;同时他投身教学,在多所学校开设“新疆考古与西域文明”课程,“力求将考古所得更准确地放置在新疆大地历史发展进程中”。
作者简介:
王炳华,1935年生于江苏,是著名的考古学家,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即投身新疆考古事业,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罗布淖尔荒原、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绿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等等,四十年如一日奔波在考古一线,主持并参与了楼兰、尼雅、克里雅、丹丹乌列克、小河等考古遗址的发掘,形成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取得了大量开创性成果,为西域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60年代初,王炳华等即对伊犁河流域进行了发掘,他提出了乌孙考古文化的概念,对当时刚起步的新疆考古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革”结束后,他主持发掘了阿拉沟的多处墓葬,并撰文详述了其为塞人考古文化的观点,极大促进了对新疆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文化遗存的讨论。1987年,王先生在呼图壁县发现的康家石门子岩画所揭示的古人生殖崇拜思想,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对新疆地区生殖崇拜和古人精神世界的研究也成为了他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后来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哈密五堡古尸、楼兰古墓沟出土的“楼兰美女”及“太阳墓”墓葬遗存所呈现出的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经由王先生的分析论述,让异质文明碰撞后产生的混融与合一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与总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炳华先生还曾组织、带领中日、中法联合考古队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尼雅遗址和克里雅河流域进行了发掘与考察。精绝王陵的发掘被评为当年(1995)考古十大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宝。2000年,王先生与考古队在骑骆驼深入沙漠第五天成功发现了小河墓地,再一次将沉睡的丝绸之路古代遗存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2000年退休后,王炳华先生仍然继续对西域文史领域的思考,追索新疆作为欧亚大陆古代东西方文化桥梁的非凡意义。在过往的发掘考察中,他曾发现大量出土文献资料,退休后对这些资料的持续关注,加上考古经验的综合运用,让他更加全面立体地检视和把握丝绸之路研究。在天山南北长时间的考察与众多发现,让王先生对古代文明遗存透露出的环境变迁与绿洲农业发展历程格外关注,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考察自然环境改变与农耕水利相关的方方面面。同时,他还对墓葬中发现的文物,结合传世史籍的记载进行分析,用考古资料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画面,阐释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与发展。
在最初奔赴新疆的时候,王先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盼望积贫积弱的祖国能够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他给自己的挑战,更是履行与坚守一名新中国考古人的责任。他对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人类文化交往进行的系统论证,使新疆考古再次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王先生始终践行着坚定的学术理想,而他瀚海行脚六十载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为这份理想交出的完满答卷。
延伸阅读:
士变:解码近代中国思想巨变的关键钥匙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转折看似悄然无声,却足以重塑一个文明的命运。罗志田教授新著《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正是这样一部力...
《羊奶煮羊羔》:一场荒诞的文学狂欢,揭示人性的真相
在当代文学的舞台上,尤里·波利亚科夫(Yuri Polyakov)以其独特的讽刺笔触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成为俄罗斯文学界...
《我想这样被埋葬》:香农·李·道迪对生命尽头的深情独白
关于香农·李·道迪(Shannon Lee Dawdy)的具体信息似乎并不广泛存在于公开资料中,这可能意味着她是一位新兴...
《布鲁克王朝》:一段东南亚传奇历史的深度剖析
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英国著名拜占庭史、中世纪史专家,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生动的叙述风格闻名...